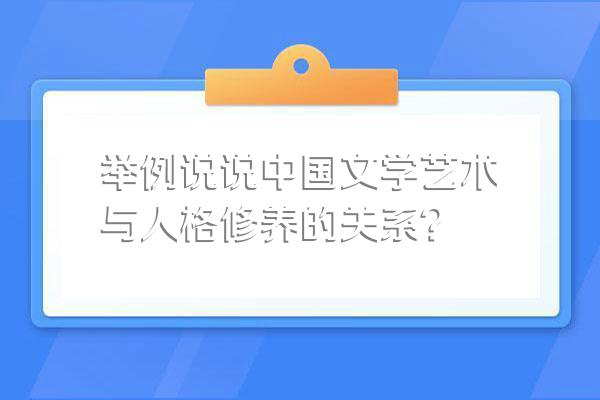
中国的文学艺术与人格修养是相辅相成的,一zhi个具有非常深厚文学艺术修养的人,其人格修养也是会达到比较高的一个层次。比如说鲁迅先生,他是我国的文学大师,但是他同样的具有爱国,关注劳苦大众,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的人格魅力。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蔡京、秦桧还是严嵩,尽管他们在书法文学上颇有成就,但因其品德败坏,其作品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中国书画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它与中国哲学紧密相连,而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因此,谈到中国书画艺术时,必须关注人品与涵养,它强调从艺者的道德修养,与人品涵养不可分割。
艺术家的修养,对于中国画而言主要作用于人文境界,同时对笔墨的气韵也有影响。中国画本身就是写哲学、画哲学,是书画家人格化的表现,是艺术家心灵映照的产物。谁的画中人文含量高,谁的作品就更能引起审美共鸣,用曾来德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能更深地“伤害”到观众。
中国古代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从诗文中可以看出人格高尚来。但人格和文格并不是一回事,不能一味地以文观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便举出潘安的例子来说明文品与人品不一致这个问题(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
宋代的艺术特质随着宋人的思想修养和人生态度的变化逐渐向内在的神韵和格致发展,形成新的审美思潮,平淡与自然因此而成为宋代艺术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平淡”美是宋人艺术观念中最普遍的一种理论自觉。
离骚经序》)认为《离骚》以香草美人来象征人格和君臣关系,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一般说来,香草通常被屈原用来比喻或象征自己的品质和修养,“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其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等。
唐君毅先生认为:“吾人知中国文人人格之形成,主要在于自然与人文之熏陶,与内心之修养,即可知中国文人人格之伟大处,皆不在其表现一往向上之企慕向往精神,而在其学养之纯粹深厚,性情之敦笃真挚,或胸襟之超越高旷,意趣之洒落自在。”唐先生的评价,真正适合说明学者型艺术家的审美追求和精神祈向。
在丰子恺看来,艺术家要具备一颗同情心,这颗同情心不但要同情有情的人类,而且还要同情世间一切无情的物类。要求得艺术的不朽,丰首先创作者要具有同情心、众生心,文艺创作者只有具备了这种同情心、众生心的人格素养,他的作品中才会被人们认可,才会具有不朽性。